中文译本在尾页里引用了《麦田贼手》里小偷说的一句话“这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总觉得我欠他点什么”。这句话当真让我鼻头一酸,生活中的拮据,以及飘离中搬家的艰辛,到最后我的书都不断的割舍掉。而有一次我突然想翻开某本书时,此书早已不再归我所有,心中郁郁不欢,对买书一事便深以为怨。可有些书我抚摸着它时,总希望这本书归我所有,能让我细细咀嚼,旁侧里的注解能详细添加,更为重要的是这值得我为它的延续添上绵薄之力。这种亏欠当真只有读书人才能体味到的。
——前言
海莲·汉芙不喜欢看小说,因为她不喜欢虚拟的。一直以来,我无法欣赏外文诗,除却部分朗朗上口又略有深意的诗文,更多时候我以一种看“洋玩意”的方式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诗词歌赋,向来诗歌地位高于其它文学作品,它以凝练、简洁,多一个字画蛇添足、冗长多余,少一个字又美中不足,白璧有瑕。但与诗歌的表达方式无关,我把《查令十字街84号》比作诗集,只是单纯的因为它篇幅短如诗歌却余味悠长、绵延。像松林之间忽闻山中古寺里传来的幕晚钟声,夏日清晨里雾散时刹那间金色的阳光扑怀,有种说不出的清爽怡人。
第一次听到这本书的名字似乎是因为北京遇上西雅图,后来这本书突然间在耳边被提到的次数有增无减。他们说这本书是爱书人的圣经。评价之高,让我鄙视。因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见识过网民们虚抬的本事之后,对所有热议的事都有种敬而远之的心态。近来探究一番盛誉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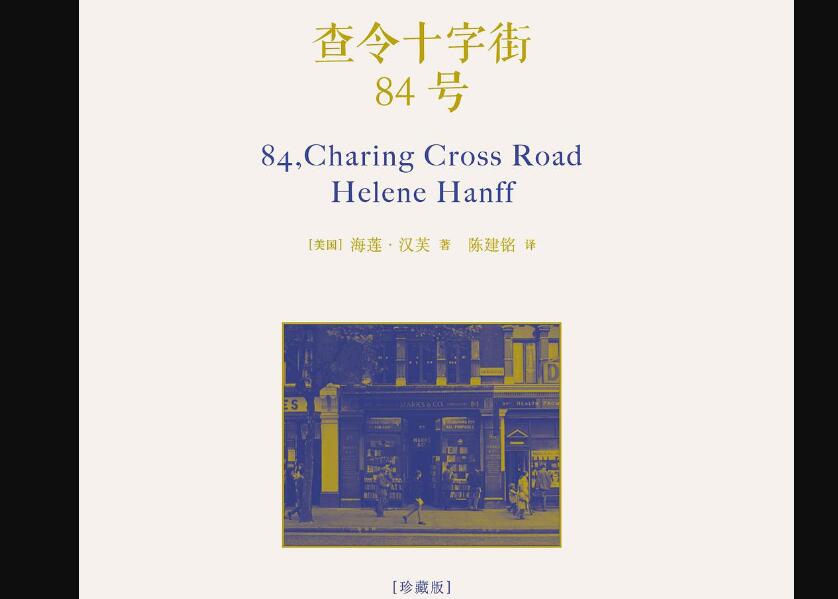
这本书,我很喜欢,并非因为故事有多婉转曲折亦或者有多感人至深,而是因为作者的每一页,每一行,每一个字都写在了我的心上。就像是海上飘着的独木舟,多年后你以为自己注定孤身一人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另一艘独木舟。译者在尾页时引用的一句话“总是在最边缘最异质的人身上,才得到自身最清晰的印记”。甚有同感,而用这句话来谈论这本书,当真是精妙之至。
“梅甘脑壳坏掉了吗?如果她真的那么厌烦文明世界,怎么不干脆搬去西伯利亚!”
20世纪里,字里行间能看出美国对俄罗斯的政治态度也渗透在民众的生活当中。海莲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并无特别的指向,但是我却为这句话里市民人物的生动形象而忍俊不禁。就像作者所说的,她非常讨厌小说,虚拟的故事太像一场骗局。而这句话里太真实的展现了上世纪的纽约。海莲从英国文学里认识了伦敦,爱上了伦敦。因为狄更斯、大仲马的小说我曾无比渴慕能亲自走进英国文学里号称事件最坚固的巴士底监狱,那众多著名“人物”为冬日里透漏出的一缕阳光而欣喜若狂,重重铁链之后的高墙里隔绝着正常生活的世界。这种对文学有着无比相似渴慕之心,让本书不得不成为爱书者的挚爱。
“我对我的编辑金谈论这段逸闻,她问我:“兰多到底是何方神圣?”我不厌其烦地为她从头细说——正当我苦心孤诣、一头热滔滔不绝时,她竟不耐烦地插嘴说“你还真的中毒不轻唉”
如果海联-汉芙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会激动的告诉她,你不是唯一一个有此经历的人!当有一日我与人谈论起武侠梁羽生时,说及金庸赠给梁羽生的挽联里写道“侠客尽仗义,仗义长存风光是,儒家多风流风流宛在梁羽生。”而今金庸故去之时,好友皆以离去,再也没有人能为他写一副合适的挽联了。我的惋惜里是朋友们听不懂的故事,对此毫无共鸣之处,寡淡无趣之际只有一层薄薄的,洗洗早点睡吧。这就好比是,当你拿着一副好牌,一个亿即将到手的时候,突然桌子裂开了,此局作废…。
海莲喜欢旧书,喜欢有前人阅读的笔记,尤其是当阅读者与她所思所想全然一致时,欢呼雀跃,并迫不及待的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弗兰克-德尔。我不喜欢旧书,厌恶书上那种年岁久远之时散发出来腐朽气息,更讨厌一群人在上面涂抹。前人将思考放在笔记里,而今难以追寻。
海莲说她不再看的书会扔掉,而我就是她所说的那一类真正奇怪的人,书看完了不再看第二遍却又不会清理掉,找一个珍贵的高隔存放起来。这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说辞,却又深以为惭愧。秉持着一种,世界上的好书千千万,我人生不过数十载,一本书看一遍就够了,不该再浪费时间去看第二遍。为此,我还找来杨绛先生的话做挡箭牌,好的诗词每一个字是有粘性的,那个字记不住一准是那个字用的不够好。好的书看一遍就会记在脑海里,怎么忘也忘不掉,因为那些话、那些故事都有其精妙之处,如果忘了肯定是那段话不够精妙。想来,我做任何事都冒进求速,往往丢三落四需费更多功夫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这么多年,也才知晓,就像男人喜欢的是女人精致的面貌,而我喜爱的也不过是书的“皮囊”。那些被翻阅过的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丝毫未能增进文学修养。景昌吉先生所说的恍恍惚惚之人,就是我无疑了。但我也很是羡慕海莲,她的“喜悦”有弗兰克可以共享,而我看到一篇好文时,通讯录翻来翻去,想想还是算了吧。
查令十字街84号的广告为何会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毕竟这家书店看起来还是挺穷的哪来的,这广告费得废掉了大家多少工资,有点心疼书店的老板和员工。通信之始,海莲直接拒绝弗兰克让她以汇支票的方式,并且还补充说道她对美国邮政非常相信。在后来的信里,好友特意绕了很远的地方以支票汇款,钱却失踪了。作文www.yuananren.com这些信件,让我觉得作者不像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个拥有着有趣灵魂的熟人。她说话的方式,谈论事情的语调,傻傻呼呼却又简简单单的与众不同之处,透露出一种率真。也只有这样的性格,才会有隔着江洋之距和另一个人成为莫逆之交。缘分的奇妙之处,总是在于其有着无数种会错过的偶然性却更有一份不可违逆的必然性。我猜想着如果那天海莲错过了报纸上的广告,她也会找上查林十字街84号,因为她对伦敦的爱会让她对这一切都无比留心。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会散,而有些人无论走多远,无需回头,知他们一直都在。
弗兰克对生活中的拮据与为难,也只是简单的一句,希望丘吉尔能够赢得选票,改善我们的生活。海莲的信,并未过多的言辞,答复的信里却也提及到恭喜丘吉尔获选。她对美国全力帮助日本与德国走出二战的阴影,却对自己的盟友不闻不问很是懊恼。并说出孩子气的话“我如果能够对盟友贡献一份力量时,我会尽力帮助,到时候美国需对我支付双倍的赔偿”。言语三三两两,就像历史学家对甲骨文上每一个字的惊喜与探究,海莲的信里透露出20世纪六十年代里西方国家的时间轨迹。我细细的窥视着,这个与严肃文学里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
政治性的东西,离我们太过于遥远,以致于很多时候政治总是在牺牲个体的感受和财产实现一种“集体”利益。部分总是高于片面,但总有一些人会坚持着一些为多数人不屑的事情,也因为这些事情改变了必行的轨径。因为有一些人会去做99%的人都不会做的事情,所以世界能够把可能性沿袭下来。而国家于个体而言不过是三三两两常走的街道,周周转转遇见的生命。有太多事总是很复杂,因此我们很难与人说清楚。所以所谓知交,不过是我想说的你都能听明白。我们当前的文化很多人总是喜欢把国与家分割开,而西方文学里会过度的注重个体。希望有一日,这两个字就像海莲的抱怨一样,能够更为融洽的走进我们的生活。毕竟今日里,这些讨论都带有严重的偏见和硝烟味。
世界所有的书籍推荐指南,总会遗忘、错过那些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著作。谁也无法否认,被遗忘过的,被大众主流所抛弃的文学著作里有着更为经典的故事、小说、诗歌。每一个爱书者,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书单而不是网络媒体的排名。我并不苟同译者对海莲写下此书的定义为,当她把这段回忆变成文字的时候,查林十字街84号将永远保留。我更倾向于,她写下了这个故事,只是喜欢这段回忆,与人类社会的习惯无关、与世界对作家的要求无关,与是否成为什么样的人无关。那么复杂的条条框框去定义一个纯粹的人,太不合适!
若非身临现场、亲眼目睹,何以让读者尽信余言。
我不必去那里,已经全信了。
或许是吧,就算那儿没有查林十字街84号,环顾我的四周,我很笃定,它们已在此驻足。
我攀上华山的时候虽未能见证华山之巅一决高下的南帝北丐、东邪西毒,但我望着苍茫重雾,耳际响起了蓉儿笑声,七公的豪言,段王爷的温煦,还有疯狂入魔的老毒物。我走过苏州的古老小巷,看着河流穿过崭新的城门,依旧能感受到伍子胥那怒火红烧的眼睛。无论去到哪里,那些书本里描述过的一切,都让我对这方圆之地都会似曾相识。它们是我所笃定的驻足。
若有一日我走过查令十字街84号,我一定会在路过时绕道远离。因为我会害怕自己看到站在书店门口想进又不知为何进去的海莲,没有弗兰克-德尔,那么伦敦的这家书店便和全世界所有的书店毫无区别。与此更为让人难过的在于,当有一日,你熟悉的人都已经远去而且杳无音讯,那么怀念和悲伤哪一个能拯救你孤独的心。会有人潇洒的说,失去过总比从未拥有过要强得多,但是又有谁能知道痛苦的失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这种折磨会是多么大的煎熬。就像一切好友离去,金庸的挽联里再无一句般配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