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来大学二年级时我们在班上搞论文(习作)报告会,就有同学选了“文学史的重写”这样宏大的题目,而当时的我对于论文怎么写几乎还停留在鉴赏的阶段。现在想来,“文学史”这样宏大、宏观的架构和琐碎细微的文本之间正如“龙”与“虫”一样,是一个纲目的两端,对举并置,雕龙还是雕虫,也许只是一体之两面。
这十一篇文章也是作者对这样两端之间张力与平衡的探讨,对我而言,特别重要的不是作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而是作者细读文本带领读者一起思考回到历史现场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有趣有益,且充满想像力的。
作者在自序中说她主要关注的内容在以下两方面:抄本文化/文本的“言说性”。这两者一偏于文献学,一偏于文学研究,但最终在试图解决文本与文学史的关系上又有内在的一致。作者的“野心”是显而易见的,文学研究首先以文献学为起点,这不容质疑,早形成共识,经过作者十余年的努力“抄本文化”无论是否得到普遍认同,这也已经成为一个让学界熟悉且不能忽视的背景词汇。被建构的文学史能否成为我们检点阅读文学作品的框架或桎梏?既然是“史”,应该是真实的,然而是否真实?这是作者不停在自问及提醒读者注意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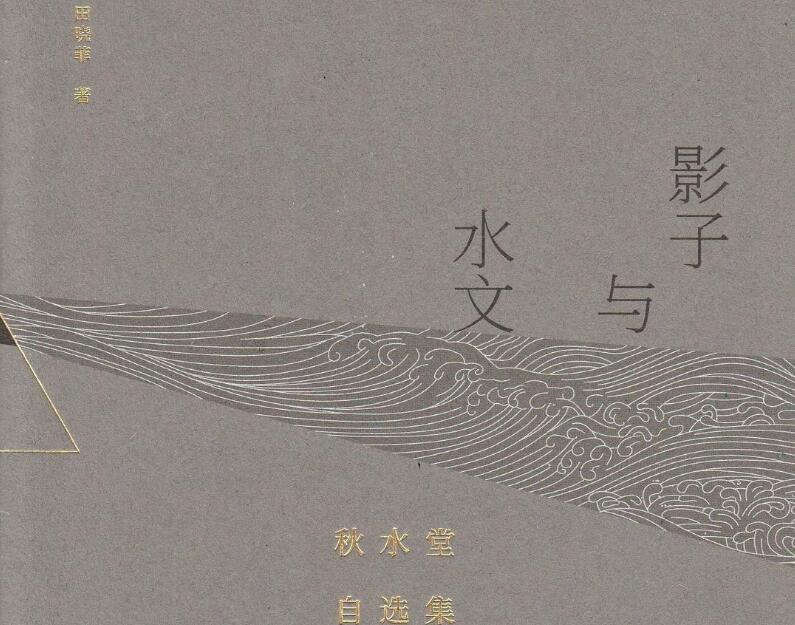
作者反复借不同的个案所要指明的,在我看来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把抄本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文本,一个历史的文本,纠正我们对于文本的刻板印象:有初始文本,有最接近于真实状态的完美文本。这一点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重造历史》一篇中,作者指出魏不仅构建了自己政治合法性的地位,也在文学上争夺了汉魏至建安、正始文学这一标准文学史的正统地位,而吴蜀文学因为他们政治上的失败在文学史中“被低音”了。文本的佚失和变形是历史文献常见的一种存在形态。佚失的文本有无价值?其价值如何体现?文本的佚失有客观的原因——战争、水火等,也有主观的原因——不感兴趣、不抄、禁毁。作者在三国的个案中所提供出来的角度是政治性的,即文本的佚失和变形某种程度上是由王朝塑造出来的。而在讨论六朝与初唐的选本这篇里,作者就认为文本的佚失和变形与文献的抄本、选本的形式相关,是由选集、总集塑造出来的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形象,这并非是基于作家全部作品的全貌。作者的比喻非常精妙形象,将类书、选本比作容器,容器的形状塑造了时代文学的形状,也影响了读者对盛放于此容器中的个别文本的解读。
作者认为“抄书”是抄本时代的一种治学方式,这点也很有启发。这在版本学上,也许就形成了一书的不同抄本,并且抄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作文www.yuananren.com对于类书在版本校勘中的作用,作者也特别修正了一种说法,即将类书版本“保存了古本的原貌”修正为“反映了古写本之一种的面貌”。由此也提出对中古抄本时代的阅读方法,即文本细读,不仅细读作者的传世文本,更要细读此传世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保存在各处的不同版本,比对其中的差异,还要熟悉该作者熟悉的文本范围,同时熟悉作者同时代的周边文本。其实,这也不仅只是阅读中古的方法,也是历史地来研究文学的方法。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是《诸子的黄昏》。作者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去探讨一个思想史上的问题。简单说,子书创作在五世纪突然衰落的原因仍然可以归因于“文学的觉醒”,这是一个老命题。田晓菲却从一些新的角度给予了新阐释。子书写作本是传统士人三不朽之“立言”之一种,曹丕所说之“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但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文具有历史感地描绘了黄昏渐暗的过程,但文学之星却随之而起,诗文写作似星光,士人有了新的途径完成“立言”的使命。我从前没有想过,《文心雕龙》、《史通》、《颜氏家训》这类书是子书的延续和变形。作者的论证言之成理。
《影子与水文》一篇大约要结合图来一起看,我看得觉得有点绕,也觉得有些阐释太过。
《有诗为证》在说“诗史”的问题。在“诗言志”的脉络里,作者选取了在晚清这个时段里分析了“诗史”这个概念在江湜、郑珍、姚燮三人的乱离诗中的表现。江湜亲历太平天国之乱,其上司惨死于前,但他所遭遇的刀痕与鲜血在其诗中是隔离的,是笼统的,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下去审视,几乎是没有任何具体而细节的呈现的。郑珍的诗写的是一对婆媳烈妇死于太平军的事迹,这里将郑诗与《府志》碑铭中的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发现了郑诗在叙事细节上的模糊、特别之处。姚燮生前为自己的诗集作了精心编纂,但他诗集中呈现出来的自我形象与同时期未收入诗集中的作品、及与其它体裁的作品中呈现的形象是割裂的、矛盾的。这三个个案作者放在一起用来检视传统“诗史”概念的崩溃。这其实是古典文学向白话文学过渡的重要一环,作者细致入微地给我们呈现了这种过渡的肌理。
总体印象,作者非常会取标题,抓人眼球。作者的研究方法是偏向历史的、田野的,有历史想像力,有超越传统文献学的野心。作者:达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