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作家,一生只写过一本书,或以一本书为人所知。我大概就是这种巴托比症候呼之欲出的作家——虽然从未试图加入组织,并且始终默默无闻。童话集《一百零一个下午》(百花文艺,2002年)出版后,文学创作时断时续,有些贴到网上,阅者寥寥——抽屉或许是最理想的读者;杨横波(197?~2008)被宣判了死刑,另外的肉体接纳了逃逸的精灵——它有着日益恶化的趣味。而《长安的春天》(中华书局,2007年)之后,我再无任何学术方面的建树,甚至在半主动半被动之间,有意无意与圈子保持了距离。纵然会有芒刺在背之感,我还是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野心:在文学创作上,我希望写得像巴别尔和加莱亚诺一样直接有力,朴素华丽兼而有之;在研究领域,我把岑仲勉、钱穆和斯坦纳视为榜样,渴慕史家学裁识笔四者皆具的境界。人偶尔要狂妄一下。我自知缺乏天赋,更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实现梦想——很多时候,我似乎是在这个世界的表面无目的地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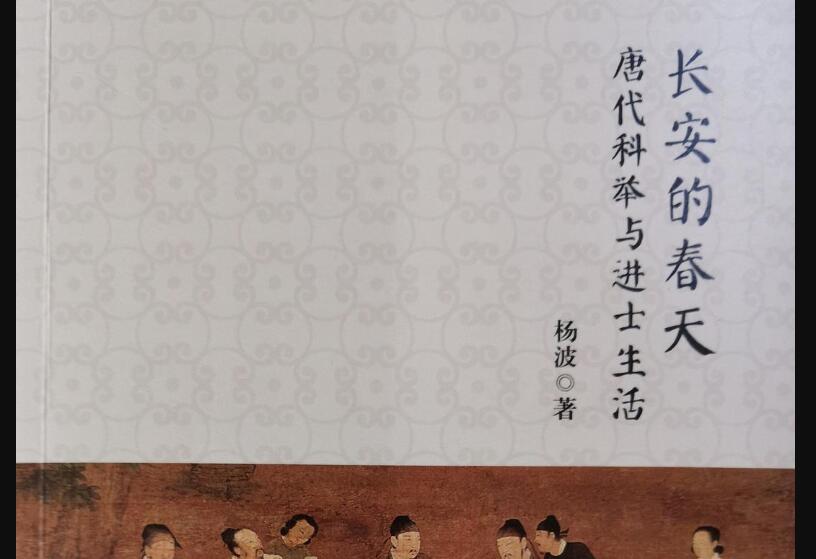
一个人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不易断言——即便是自我审视——但书的成败可以。本书是一部失败之书。首先,它让作者不满意。作者浑身毛病:重度拖延症,中度强迫症,轻度抑郁症,再加上无药可解的没头脑和不高兴。所以世间万事万物难有令他完全满意的。其次,作者数度中夜自省,终于认清了一个他长期以来不肯面对的事实:不学而无术。不学,因之如夏虫井蛙,一捉襟便可见肘;无术,所以似盲人瞎马,才临深复又履薄。再者,世间之书,泰半灾梨祸枣——用时髦些的话说,不低碳——属于可烧之列,虽然焚书无论如何是野蛮的。最后,失败是失败之母。不需要为失败寻找借口。几百年前,全椒人吴敬梓通过小说书写为自己的世俗失败辩护,本书的作者,古虞人的后裔,也是如此,只是他用于自辩者不幸也是失败之作。
这样一部失败之作,出版方将它从图书的深海中打捞出来,颇令人意外;考虑到百花社与我的多重因缘,此举又顿失悬疑色彩。沉埋已久的旧作重见天日,《长安的春天》再度逢春,端赖汪兄惠仁之鼎力促成。朋友当中,他的能言善道博洽多闻无人可及——秦小雨同学差可争一日短长;多日不见,听闻他日理出版万机之余,以书法遣兴怡情,想必泼墨挥毫之际,胸中仍存丘壑与烟云。我曾经很认真地写下了这部注定是失败之作的每一行文字,如今又同样认真地校订了每一行文字。内容无足轻重,但文笔还算可观。这是聊堪自慰的,或许也能不负出版方的厚爱,以及文字和美术编辑的辛苦。
此书再版,恰值恩师孙昌武先生的三十卷文集由中华陆续推出,不肖无面目登门道贺,唯有内心遥祝;予我身教言传的陶师慕宁和李师剑国,虽臻老境而风采依旧;傅璇琮先生却早已驾鹤西归,思之能不凄然。
修订工作始于七月中,八月底毕其事。大的框架没动,只是核校了引文,改正了错误,增补了注释和某些段落,撤换了大部分图片,作文www.yuananren.com恢复了中华版删去的参考文献并做了必要的更动添加——很多书替用了最新版本(其中不少来自网络下载,对那些扫描并慷慨分享它们的人,我心怀感激和敬意,如果学术已然是一个帝国,那么他们就是勇于挑战体制的英雄海盗)。最大的变化,是《过夏》一节,在一篇未发表旧文基础上几乎重新写过。不是为了让它显得更学术,仅仅是个性使然。
但这本书并非一本新书。不学无术的我,也不清楚怎样将之变成专著。评价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唯一的标准是好与坏,而不是出版单位级别的高低或刊物是否核心。学校官本位,学术工业化,人们也丧失了好坏是非的判断力。
多年以来,我差不多过着一种伪隐士的生活。我依法纳税,因此不算真正的隐士——根据西尔万·泰松的说法,归隐便等于反抗。在监视器和探照灯无孔不入的时代,隐根本上是不可实现的。而我所从事的研究,说穿了,百无一用——准确而言,用途是有一丁点儿的,就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花边和点缀。
假如生在大唐,我可能在风陵渡口等船的时候,西望长安的浮云,回看家乡的晨阳,然后跨上驴子缓缓归去。假如生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洪荒,无论从体力或智力看,我都会是第一个被淘汰的。我这样的人,在古代是异类,在现代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