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当然不是说,书写历史的人,写的都是当下的事。那就不叫历史了。我想,这话所言,是指史书里对人物的评点与书写,往往都体现出作者所处当世的价值观念。书写人物,免不了有所臧否,即使作者力求公正、客观,也免不了在行文间,流露出自己的态度。
更何况,中国的史书往往承载着道德教化的责任。修史的士大夫自谓为四民之首,总以教化人心为己任,写起书来,喜欢选取那些能教化人心或警惕世人的故事。经常还跳出来,对人物进行直接的点评。在这些点评里,有时候,就能看出时代变迁后,价值观又发生了什么改变。最近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就很有这种感觉。
公元前二三三年,在韩国郁郁不得志的韩非子被做为使者派遣到秦国。他入见秦王,表示自己愿意为秦国出力,并且许下豪言壮语:“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简单来说:我给您办事,事办不成,您办了我!
然而韩非子还没来得及开始办事,就被李斯陷害,毒死在了监狱中。司马光在书中说: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意思就是说,韩非这个人,身为韩国人,为秦国出谋划策,竟然想要覆灭自己的宗主国韩国(韩不亡...大王斩臣以徇国),死不足惜,不值得怜悯。
对于身处于大一统帝国,从小接受儒学教化,满腔爱国爱君主义的司马光来说,韩非子这样子的人,岂止“乌足愍哉”,简直应该千刀万剐才是。毕竟大一统帝国,讲求的是对皇帝和国家的绝对忠诚,一个人应该无限地臣服于自己的国君,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才是臣节所在,大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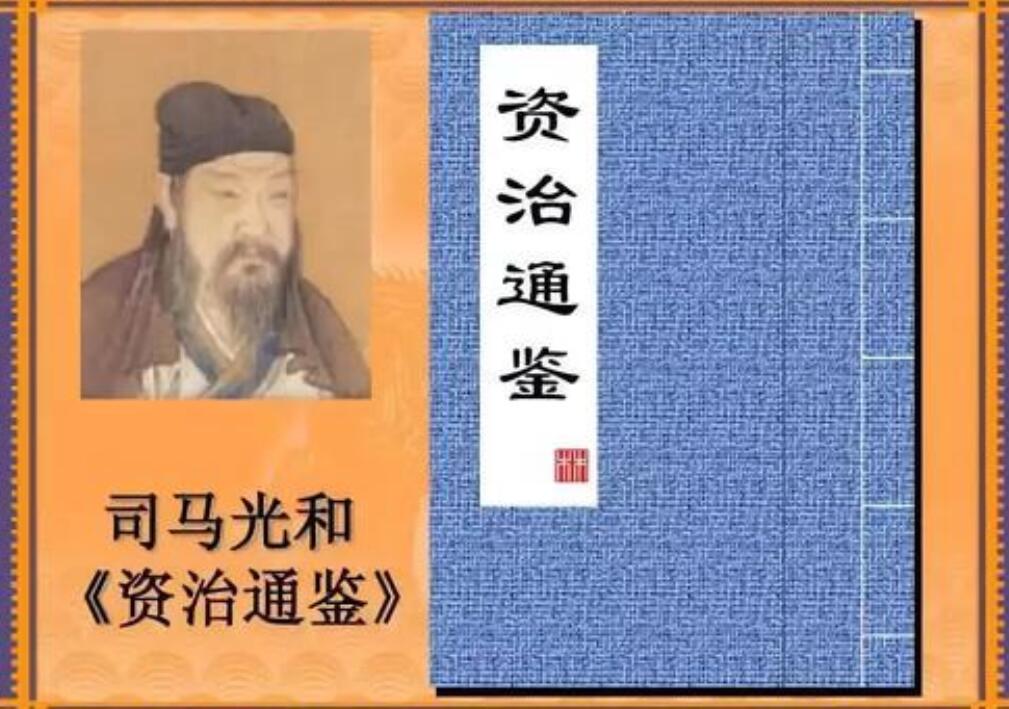
而韩非子呢,因为在韩国,得不到重用(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又见到韩国朝政日非(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就开始写文章传播负能量(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最后还因为秦王欣赏自己,就跑到秦国去献策。
对于司马光来说,这大概就好像说王安石上书变法,不被大宋准许,就跑到契丹去搞改革一样,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虽然秦国不是胡虏,但为了个人抱负的施展,而弃家国大义于不顾,委身事敌,韩非于司马光来说,大概不免被视为“贰臣”。
但仔细看一看春秋战国的历史,这样的“贰臣”并不鲜见。伍子胥由楚入吴,还可说是有毁家之恨、杀父之仇,魏国的公孙鞅,跑到秦国当商鞅搞变法,可就不是因为遇到什么危险了,明明魏王都不想杀他,可他帮着秦国富强,可是把魏国打惨了。
即使看看儒家的祖宗们,亚圣孟夫子,也是“不远千里”地来回奔波于魏、齐之间,孔夫子他老人家也没有乖乖待在鲁国,而是到处周游列国,想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哪个人能当伯乐,识得他这匹千里马,他也是愿意供其驱使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话,跟阮氏三雄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结起来,与大一统帝国下,对人臣必须绝对忠诚的要求相比,春秋战国的士大夫效忠君王,都是有条件的,你得是能欣赏能重用的“贾者”,而不是单纯因为我生长于某国某地,便可以要求我无限地效忠。
礼贤下士,不仅是君王们的美德,更是士人服务的必要条件。古人常叹世道浇漓,是人心不古。现在看来,人心太古了,对统治者来说,作文www.yuananren.com未必是好事。所以朱元璋要删改《孟子》,像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讲条件的言论,对君王保持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大大地不利,自然不能留存。
也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言论,在没删改前,怎么没把后世的腐儒们吓掉脑袋。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有人说,“爱国”和对国家“忠诚”是要讲条件的,而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一个人换国家可以像换公司一样,要看福利、看条件、看企业文化符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看企业主是不是足够尊重自己,让自己在这里能有尊严地发挥自己,估计也会触犯到很多人那颗敏感而脆弱的爱国心。
可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中国的士人们曾经这么生活过,他们面对着纷乱扰攘的诸侯纷争,也想为自己所出身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当自己的国家无法欣赏自己、重用自己、尊重自己,感到生命和才华被浪费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选择毫不留情地离开,去寻找那个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舒展的所在。
对于他们来说,那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才能成为自己服务的对象,那个给自己尊严的所在,才是自己的祖国。到了大一统帝国的时代,四海宾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地理上几乎消除了士人们选择的可能。同时,统治者们还要从思想上消除掉选择的想法,要告诉人们,“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一个政权即使腐败无能,对自己不公与迫害,自己能做的也只是“文死谏”。《弟子规》里说子辈对父辈应该“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寻常父亲,尚且要如此对待,更何况面对君父?
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士人们还能站在统治者面前,说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的话,要求自己作为一个个人必须得到尊重,才能贡献自己的才华,如果被视为“土芥”,就可以把折辱自己的那个人当成“寇仇”。
而到了六百多年前的明朝,皇权发展到了极端,廷杖成为了一种制度,皇帝可以因为自己不爽,当庭折辱大臣,而且要求对方必须嘴啃泥。无数大臣被当场拉下裤子打屁股,这样的场景,有明一代,不绝如缕。作为帝国的臣子,被打屁股意味着他们直言敢谏,所以才触怒皇帝,是朝廷的直臣,皇帝的忠臣。所以,作为一个人越被折辱,则作为一个大臣越有尊严。如王小波在《个人尊严》一文中所说: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
那些先秦士人所坚持的个人尊严,在那些大臣们被扒下裤子的时候,早已被剥夺殆尽。只剩下作为臣子身份的尊严。我很怀疑,今天很多人口中的“爱国”,也不过是这种被打屁股还觉得与有荣焉的爱国,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一种觉得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忠诚。
公元前二二七年,荆轲来到秦国,向秦王献上地图和樊於期的头颅。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图穷匕见,功败垂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太子丹和荆轲的评价都不高,太子丹是“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的罪人,荆轲是“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的愚夫。不仅如此,要离、聂政等人,在他眼中,“皆不可谓之义”。
可千百年来,依然有许多人在称许像聂政那样因为“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而感动,最后为了严的私仇而献出生命的侠客。
大概是,在个人尊严一直被漠视、被践踏的社会,那些“豢养之私”式的敬重,就足以让人们萌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所以先秦时代,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豫让杀身,专诸刺僚,荆轲刺秦而被戗,候赢窃符而自杀。这些一直被广泛传颂的先秦侠客们,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也许不懂得什么国家大义,只是因为一点“豢养之私”,就敢于为敬重自己的统治者献出生命。
我们自古以来,从不缺那些敢于献身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缺失的,往往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能够给予人们足够尊严的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