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启示哲学导论第八讲结尾处的表述来讲,晚期谢林所要处理的是有关纯粹的表象活动(存在)和纯粹的思想活动(概念)的问题。只要谢林不愿意像黑格尔一样放弃直接给出表象活动的根据,把表象看作是自规定的运动,进而仅仅在诸表象的联系中把握表象的根据(这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尽管黑格尔也可能会在最后承认根据是无据的,就像齐泽克指出的那样),他就必须去直接思考表象本身的纯粹偶然性并把这种偶然性与其他者——概念——严格对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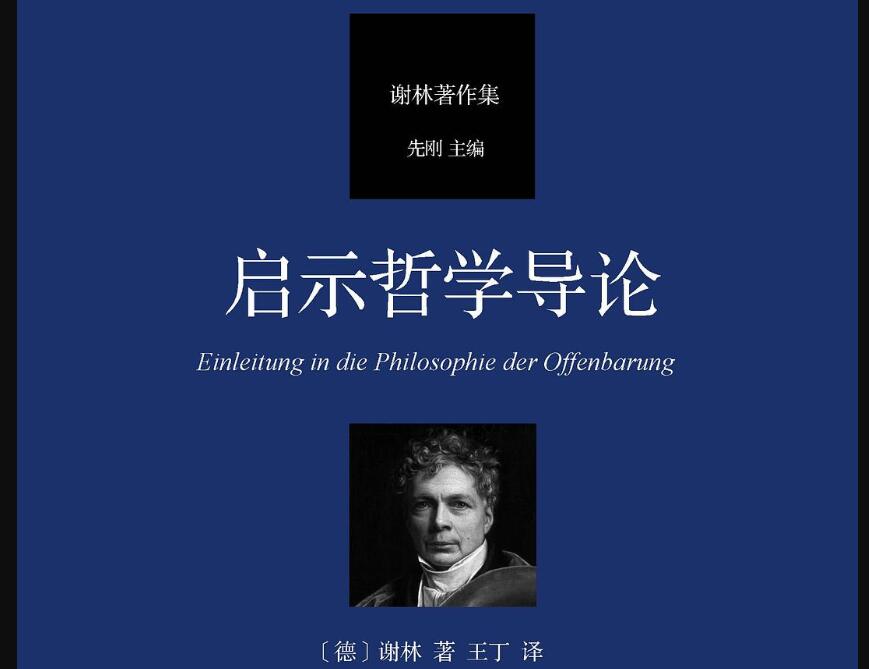
这样做的后果是,谢林就直接取消了概念的现实存在(因为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是绝对偶然的,谢林反复强调这点,它属于前者)。这也就把谢林带入了一个僵局中:单纯的存在和单纯的可能互相对立,但彼此又漠不相干。为了突破这个僵局,后期谢林采取的方法是引入上帝作为绝对自由的行动者来进行这两者之间的联结活动,通过让“上帝悬置纯粹存在而进入到自己的概念中”使得这对立的两者形成一个统一体,现实的存在者——它既是实存的,也是可被概念把握的。顺便,这也是恩格斯对谢林的批评的出发点,简单地说,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恩格斯认为谢林人为地将概念和存在分离开来,以便拿上帝的自由取代概念的必然性——从某种意义看上可被理解为存在者必然地被“辩证地”颠覆的规律,从而指责谢林地哲学是反动的。
但并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把谢林的上帝思考为一个类似于“大他者的大他者”的形象,即一个绝对的本原。必须强调的是,谢林绝没有直接设定上帝并以此为起点开始演绎(谢林反复提到不同于经院哲学家的上帝,自己的上帝是后天的),他首先把上帝看作是“一种假设”,作文www.yuananren.com只有当“一切我们已将之证实为后果地东西已然作为现实之物存在”时,假设才“不再是假设”了。那么这也就是说,谢林所真正的关注的还是现实之物(并不完全如恩格斯所言是个胡思乱想的神秘主义者),但他又希望能超出现实之物的在场而思考它们的发生学问题——这也就是他和黑格尔不同的地方。与之相对,真正在谢林那里被直接设置的是存在,即所谓不可预思之物,前现实的无据深渊。
而恰恰是这一深渊构成了现实的根据,它在上述现实化的过程中“在其根基上并不会被取消”。而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思考这个无据性的出发点必须是已经实存的现实的存在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谢林要在存在之外再引入作为纯可能性的概念,因为可被概念把握的存在者确实就是实存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谢林所作的无非是“解释存在者”并把其看作是作用在纯粹存在上的一个行动的结果(创世行动)。
一言以蔽之,这本书完成了两个任务:一是否定哲学批判:指出现实构成性上的根本的不完备,故而总有某种纯粹的偶然性(存在)无法被批判的理性完全穿透(无据);二是肯定哲学:将存在向存在者的过渡回溯设定为上帝意志的结果。
